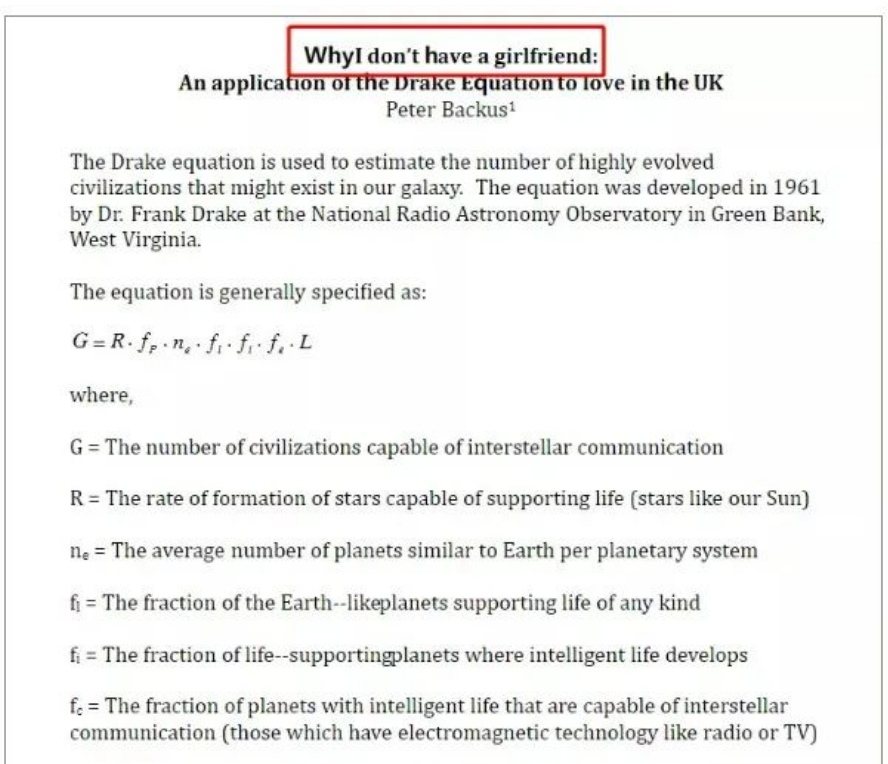每年三四月份研究生论文审读定稿的时候,导师们的“吐槽”声总是不绝于耳。这也难怪,平时看上去古灵精怪、口吐莲花的学生,写出来的论文却是语言贫乏,词不达意,疙里疙瘩,搞得师徒一起着急上火,寝食难安。几经修改润色,直到使论文在表面上“看上去挺美”,才敢长舒一口气,定稿交稿,在焦虑中等待后续的评阅和答辩。
经此“磨难”的老师,在感慨“带学生很难”之余,也会发誓以后要“高标准,严要求”,在平日里就督促他们读书写文章,只是决心易下,执行挺难,等到下一届来学生入学了,依然是放养为主,学生们呢,巴不得你想不起他来,放养的模式自由而快乐。读研这事确实挺苦,你得有研究的兴趣和天赋,还要能坐得住冷板凳。只可惜现在的读研成了延迟就业的“缓刑期”,且找工作时还可以因研究生的学历而增强竞争力。所以考研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。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是研究生复试的时节,学生们要参加各种面试笔试培训班,还得到处打听调剂的信息,而且现在是一人考研,全家上阵,陪考陪复试,投入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,由此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种考研经济。经历了如此的艰难才获得了读研的入场券,到毕业时论文却是那般难产,个中缘由,大概只能到“过程”中去找了。俗话说“师父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”,似乎是说成不成器,关键在于学生个人的努力。这话虽然不假,但也有点儿“师父”推卸责任的意味。就说写论文这事吧。其实对于研究生来说,上过几门课,成绩多少并不是很重要,能不能毕业关键就是看论文写得怎么样。而对于平常练笔少,积累又不多的学生来说,要想写出篇像样的文章来着实不易。选题不易不说,即便选好了,因相关知识储备不足,也无法使文章变得丰满且言之有物。因此,博览群书是必须的。温梓川(“必记本”注:曾在中山大学、暨南大学就读)先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,他的“朋友圈儿”里可都不是一般人,他和郁达夫、曹聚仁等交谊甚笃,和梁实秋、沈从文、徐志摩等亦过从甚密。在其《文人的另一面——民国风景之一种》里,温先生记录了他的老师冯三昧(“必记本”注:先后在上海大学、暨南大学任教)对他走上写文字道路的引导。他说在冯的课堂上,曾写了一篇小说,交给老师几天后,老师约他去喝茶,并让他看一个日本作家的小品。等温看完后,居然发现他自己的小说和日本作家的文章很相似,不过这并不是抄袭的问题,而是碰巧构思或利用了同样的题材。冯先生的教导是这样的:“既然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与人家的作品有巧合之处,那么作品大可以作废了的,写作要言人所未有才能够代表你自己。以后,你至少要先读完了一二百本外国小说才动笔,那么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所要说的东西,有没有人说过了,应该怎样着眼于人家所未知的东西了。要从事写作,绝对不能贪懒的。”其实写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!发现别人不曾研究过的专题,然后做下去,才会有新意。所以准备写论文的学生,至少也该读几十部本专业的经典。在法言法,法学的研究生自然应该去读大量的法学经典。当然,如果师父不仅是领进门,还督促你“修行”的话,即便资质平平的学生,也会学有所成。现在这样的导师少了,但也并非没有。前几年有位年轻人在复旦读古典文学的博士,她的导师已经70多岁。老先生要求他的学生每周见一次面,汇报上周都读了什么书,有什么心得,下周准备读什么,督促得紧着呢。博士生说她和同门师兄妹最怕的就是见导师,每次见导师前,有的会习惯性地肚子疼。他们那几个学生,每天都会乖乖地早起,然后早早地坐到图书馆看书。这是因为她们的导师起的也很早,图书馆开门后,他就进去逛一圈儿,看到他的徒弟们都在,就满意地回家;如果有谁没在那里,他就会亲自去宿舍敲门,直到把羞愧的大懒虫叫到图书馆为止。像这样负责任的博导还真是少见。一般的导师大多洒脱自由,学生们自然也乐得潇洒,过得滋润。只是这样一来,三年以后的论文是个什么样子也就能想象的出了。复旦的这位博士生,在平日里也不乏对严厉导师的抱怨,可是在成果频出且顺利毕业的时候,她对导师却是万分地感激。大学里的导师和研究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?情同父子母女的要求有些伪善,亦师亦友尚能勉强。我倒是很赞同一位法学教授的看法,她说导师和学生就是“一篇论文的关系”。这话听起来似乎薄情,不过,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生批量生产的时代,做导师的若能督促学生静下心来,好好地读一些书,不必复制粘贴就能写一篇有自己观点,能被本专业领域专家认可的论文,顺利地毕业,又能被用人单位痛快地接收,就已经是尽了导师的本分,能做到这点,就是对学生的负责,也是对社会的负责。
来源:作者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建红,首发“北京青年报”。内容仅做学术分享之用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若涉及侵权等行为,请联系我们删除,万分感谢!